發(fā)布時間:所屬分類:文史論文瀏覽:1次
摘 要: 摘要:作為20世紀(jì)中國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潮之一,現(xiàn)代主義及其理論批判構(gòu)成20世紀(jì)80年代文論的重要內(nèi)容。總體上看,現(xiàn)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過程伴隨著雙重焦慮:被延遲的現(xiàn)代化焦慮與民族文化主體性焦慮。由此造成的現(xiàn)代主義與民族主義、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
摘要:作為20世紀(jì)中國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潮之一,現(xiàn)代主義及其理論批判構(gòu)成20世紀(jì)80年代文論的重要內(nèi)容。總體上看,現(xiàn)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過程伴隨著雙重焦慮:被延遲的現(xiàn)代化焦慮與民族文化主體性焦慮。由此造成的現(xiàn)代主義與民族主義、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內(nèi)在張力結(jié)構(gòu),成為中外學(xué)者探討中國現(xiàn)代主義的基本二元論框架。這些二元論架構(gòu)帶來了啟示與盲點(diǎn),將性別維度植入中國現(xiàn)代主義文論,在全球本土化視野中洞察現(xiàn)代主義的權(quán)力關(guān)系及其性別修辭,即可在揭示現(xiàn)代主義文藝隱含父權(quán)無意識的同時,嘗試建立現(xiàn)代、民族與性別互動對話的三維理論結(jié)構(gòu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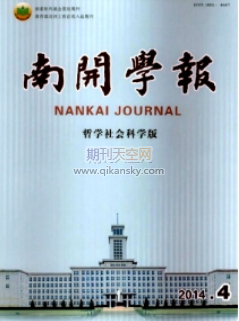
關(guān)鍵詞:現(xiàn)代主義;民族寓言;性別
現(xiàn)代主義是20世紀(jì)中國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潮之一。一方面,由于現(xiàn)代主義與西化、世界化關(guān)系密切,使之在激切追求現(xiàn)代化的中國,往往作為一種進(jìn)步文藝形態(tài)而具有天然合法性;另一方面,現(xiàn)代主義訴諸內(nèi)面性的個人主義訴求,又與現(xiàn)代中國的感時憂國傳統(tǒng)相捍格,使之不得不屢受質(zhì)疑。這個矛盾狀況導(dǎo)致現(xiàn)代主義文藝實(shí)踐在現(xiàn)代中國時斷時續(xù),相關(guān)評價也往往在肯定與否定的兩個極端擺蕩。中國社會主義文藝沒有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(tài)的經(jīng)典現(xiàn)代主義的位置,不過,這并不意味著現(xiàn)代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文藝中的缺席,社會主義文藝的超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面向,使之亦具有區(qū)別于西方經(jīng)典現(xiàn)代主義的另類的現(xiàn)代主義特征,但在日后的文藝批判中,卻被作為反現(xiàn)代的落后文藝而受到否定。
一般認(rèn)為,經(jīng)典現(xiàn)代主義在中國的復(fù)興發(fā)生在20世紀(jì)80年代,它是改革開放的中國融入西方世界、重啟現(xiàn)代化項(xiàng)目的文化表征,現(xiàn)代主義文藝及其理論生產(chǎn),由此成為8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建構(gòu)的重要內(nèi)容。縱覽幾十年來圍繞中國現(xiàn)代主義展開的理論建構(gòu),就會發(fā)現(xiàn)“民族”與“現(xiàn)代”所構(gòu)成的相反相成的二維結(jié)構(gòu),是中外學(xué)者展開論述的基本二元論框架,無論是渴望現(xiàn)代論、民族寓言論、中國主體論,都在這個二元論架構(gòu)下展開,并由此構(gòu)成一個相對封閉的霸權(quán)性研究范式。實(shí)際上,在民族與現(xiàn)代、國家與個人的二元架構(gòu)之外,性別作為奠基于社會實(shí)存的重要研究方法,也是中國現(xiàn)代主義文藝的結(jié)構(gòu)性內(nèi)容,但卻在既往的理論生產(chǎn)、文化詮釋中隱而不彰。將性別作為第三維度介入中國現(xiàn)代主義的理論生產(chǎn),建立一個由現(xiàn)代、民族與性別構(gòu)成的三維結(jié)構(gòu),有可能是重估中國文學(xué)現(xiàn)代性進(jìn)程、再造本土研究范式的有效途徑。
一、現(xiàn)代主義與民族復(fù)興
1987年12月10日,香港大學(xué)、香港中文大學(xué)和香港比較文學(xué)學(xué)會聯(lián)合在香港主辦了“第五屆國際文學(xué)理論研討會:中國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與現(xiàn)代主義研討會”①,出席此會的海峽兩岸和海外學(xué)者、作家和批評家有五十多人,大陸的有鄭敏、袁可嘉、謝冕、李陀、黃子平、季紅真、許子?xùn)|、吳亮、錢中文、王寧、王安憶、劉索拉、顧城等。大會的中心議題是(中國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與(西方)現(xiàn)代主義的關(guān)系。研討會上,大陸和海外學(xué)者在一些基本議題上存在一定爭議:一是關(guān)于女權(quán),大陸女作家王安憶和劉索拉以不同方式發(fā)表了一個類似“我不是女權(quán)主義者”的宣言,這讓一些海外學(xué)者非常不解。②遺憾的是,這一爭議并沒有延伸至大會的中心議題——現(xiàn)代主義,現(xiàn)代主義討論一開始就缺少一個必要的性別矢量。一是對于現(xiàn)代主義的情感態(tài)度:周蕾對謝冕論文《現(xiàn)代主義:中國與西方》中的“感情結(jié)構(gòu)”不以為然,認(rèn)為其理解現(xiàn)代主義的方式與現(xiàn)代主義正相反。對于現(xiàn)代主義的情感態(tài)度問題在后來的討論中得以充分展開,海內(nèi)外對現(xiàn)代主義理解的差異與錯位,也使隱藏在現(xiàn)代主義論述背后的不同的文化政治得以顯現(xiàn)。從這個意義上來看,香港的現(xiàn)代主義研討會值得關(guān)注。
謝冕論文的主要觀點(diǎn)包括:現(xiàn)代主義在中國從“斷裂”到“對接”的變化,源于“藝術(shù)反抗主義”的訴求與“重返世界的愿望”;中國文學(xué)接受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有其歷史契機(jī);現(xiàn)代主義為中國文學(xué)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;中國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對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的繼承,仍然是“中國式”的。③“中國式”指的是“特殊的本土經(jīng)驗(yàn)和感受”,是“文革”造成的破壞性的震驚體驗(yàn)。在謝冕這里,(西方)現(xiàn)代主義主要被看作一種文學(xué)手段和書寫方式,是文學(xué)的形式與結(jié)構(gòu)問題,這種對現(xiàn)代主義形式與內(nèi)容進(jìn)行的分離式接受法,在當(dāng)時相當(dāng)普遍。當(dāng)然,分離式接受并不意味著現(xiàn)代主義的中國接受者真的認(rèn)為二者可以分離,而更多是對曾作為冷戰(zhàn)禁忌、資產(chǎn)階級意識形態(tài)表達(dá)的現(xiàn)代主義的辯護(hù)策略,這種策略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現(xiàn)代化過程中“中體西用”思想的體現(xiàn)。
雖然論文題目將現(xiàn)代主義明確置于中國與西方的二元架構(gòu)內(nèi),但謝冕的意圖卻不在于呈現(xiàn)本土/中國與異域/西方之間的對抗性。(西方)現(xiàn)代主義給(中國)文學(xué)可能帶來的文化主體焦慮,此時遠(yuǎn)不及告別“文革”、走向“新時期”的愿望更為迫切。現(xiàn)代主義論述的中國/西方的外部二元架構(gòu)于是被置換為“文革”“/新時期”的內(nèi)部二元架構(gòu)。雖然他也提到了現(xiàn)代主義的“中國式”與“本土經(jīng)驗(yàn)”問題,但“本土”訴求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而非對抗(西方)現(xiàn)代主義,謝冕“中國與西方”架構(gòu)內(nèi)的現(xiàn)代主義體現(xiàn)的是一種具有普適性的現(xiàn)代主義思想,而中國經(jīng)由努力可以達(dá)至這種普適性的現(xiàn)代主義。《現(xiàn)代主義:中國與西方》體現(xiàn)了一個詩評家的獨(dú)特氣質(zhì),飽含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澎湃激情。
但正是這種彌漫于20世紀(jì)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之中“被延遲”的現(xiàn)代主義焦慮與“走向世界”的新想象,引起了評議者、時為美國明尼蘇達(dá)大學(xué)的周蕾的關(guān)注,她敏感地意識到論文在“客觀結(jié)構(gòu)”外,還有一個“感情結(jié)構(gòu)”。就此,她提出疑問:“為什么我們要用‘回歸’、‘重返世界’這樣的觀念去形容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呢?要是‘現(xiàn)代化’的真正意義(應(yīng)該發(fā)揚(yáng)光大的意義)是多元化、復(fù)雜、甚至是矛盾的思維,那為什么在中國文學(xué)重新開始實(shí)行這個‘現(xiàn)代化’的時候,我們要用一種看似非常單一的概念去理解它,把中國文學(xué)說成‘棄兒’找到家一樣?這種單一的感情的結(jié)構(gòu),與‘現(xiàn)代化’是不是相反的呢?”①周蕾質(zhì)疑了謝冕對現(xiàn)代化、現(xiàn)代主義的理解,認(rèn)為“單一的感情結(jié)構(gòu)”體現(xiàn)了對現(xiàn)代化的單一化理解,而現(xiàn)代化在周蕾看來則是多元的。周蕾對用“單一的感情結(jié)構(gòu)”來理解現(xiàn)代化的警惕,對中西看待中國現(xiàn)代化的兩種不同情感方式——“棄兒重投母親懷抱”與“老處女最后不得不打開”——的并置與質(zhì)疑,約略看出其批判西方中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后殖民立場。
從小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、生活在境外的美國學(xué)者周蕾自然難以理解內(nèi)地學(xué)者對現(xiàn)代主義的這種“情感結(jié)構(gòu)”,正如身處現(xiàn)代主義/現(xiàn)代化焦慮中的大陸知識分子,也很難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這種“感情結(jié)構(gòu)”。不過,周蕾只注意到內(nèi)地學(xué)者一廂情愿接受與追隨現(xiàn)代主義的一面,而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追隨和接受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民族復(fù)興的訴求。從徐遲的《現(xiàn)代派與現(xiàn)代化》、高行健的《遲到了的現(xiàn)代主義與當(dāng)今中國文學(xué)》到李陀的《現(xiàn)代主義與尋根》,現(xiàn)代主義的倡導(dǎo)者從不缺乏民族主義的內(nèi)核,只是在這個時期,民族主義與現(xiàn)代主義不僅并行不悖,而且是現(xiàn)代主義得以在中國流通的重要合法性來源。盡管不無誤讀成分,但周蕾對現(xiàn)代化的冷靜態(tài)度與批判立場,卻有可能警醒局內(nèi)的內(nèi)地學(xué)者,這可能是周蕾短評與謝冕論文后來同時刊發(fā)于《文學(xué)自由談》的原因吧。
現(xiàn)代主義接受中的“情感結(jié)構(gòu)”后來在許子?xùn)|的《現(xiàn)代主義與中國新時期文學(xué)》中得到深入分析。他看到中國評論家很少考察現(xiàn)代主義不同“派”之間的差異,而更關(guān)心現(xiàn)代主義與“我們”的關(guān)系。這個“我們”,在許子?xùn)|看來,至少包含(階級)政治、時代、民族這三種立場,只是各有側(cè)重隱顯,構(gòu)成極為微妙的文化景觀,而民族文化的危機(jī)與使命感,則是倡導(dǎo)者的重要合法性來源。現(xiàn)代主義在進(jìn)入中國的同時就被“我們化”了,無論反對、保留還是支持現(xiàn)代主義,都從不同角度參與著現(xiàn)代主義的“我們化”過程。將現(xiàn)代主義“階級化”在“新時期”已是明日黃花,而“更堅(jiān)定更熱忱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場”才是一種更順應(yīng)人心的“情感愿望”。民族主義的情感愿望貫穿于中國現(xiàn)代主義實(shí)踐的始終,許子?xùn)|認(rèn)為,早在1982年“四只小風(fēng)箏”通信時,李陀在贊同馮驥才熱情呼喚現(xiàn)代派的同時特地將“我們”的“現(xiàn)代小說”與“洋人”的“現(xiàn)代派”之間劃了界線,目的是希望“我們的現(xiàn)代主義”與民族文化更多結(jié)緣。②
最早明確提出“中國式的現(xiàn)代主義”的是對中國現(xiàn)代派作家影響最大的袁可嘉。還是在這次會議上,袁可嘉提出并闡明了“中國式的現(xiàn)代主義”的基本性質(zhì):“應(yīng)當(dāng)是與社會主義的現(xiàn)代化建設(shè)相對應(yīng),在最深刻的意義上為社會主義(而不是最表面意義上)、為中國人民服務(wù)的;是與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精神相溝通的,是與民族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相融合的,同時又具有獨(dú)特的現(xiàn)代意識(即現(xiàn)代化進(jìn)程中中國人的思想感情)、技巧和風(fēng)格。”③袁可嘉的“中國式”現(xiàn)代主義是中與西、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、民族與階級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、風(fēng)格與意識等的調(diào)和。但如何混合、怎樣實(shí)現(xiàn),這種“中國式”的現(xiàn)代主義是否還是現(xiàn)代主義呢?于是,在各種提倡“中國式”“我們化”現(xiàn)代主義的同時,是對中國的現(xiàn)代主義文學(xué)還“不夠現(xiàn)代主義”的抱怨與批評。香港會議上,季紅真在比較中國現(xiàn)代派創(chuàng)作與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的基礎(chǔ)上,認(rèn)為中國沒有出現(xiàn)嚴(yán)格意義上的現(xiàn)代主義文學(xué)。④這呼應(yīng)了國內(nèi)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的“偽現(xiàn)代派”說法。黃子平則分析了“偽現(xiàn)代派”批評與“純現(xiàn)代派”要求背后的悖論,認(rèn)為這是試圖剝離自身的體驗(yàn)和文化以遷就或達(dá)到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的完整性的做法,那些把現(xiàn)代派文學(xué)營養(yǎng)吸收更好的作品,恰恰不在技巧,而在于對人生、世界的某種共通的體驗(yàn)。①黃子平討論現(xiàn)代主義的方式,在許子?xùn)|看來,“標(biāo)志著中國評論界對于現(xiàn)代主義問題的一種冷靜的專業(yè)研究態(tài)度的出現(xiàn)(而不再象過去那樣每種意見首先意味某種情感愿望)”。②
于是,許子?xùn)|一方面肯定現(xiàn)代主義“我們化”過程中漢民族的民族文化本位是一種更順應(yīng)時代的情感愿望,一方面又警惕“情感愿望”在“我們化”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會產(chǎn)生的問題:“‘我們’當(dāng)初曾經(jīng)那么急切地消化改造了西方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這種‘異質(zhì)’文化,要求立刻‘為我所用’,結(jié)果十九世紀(jì)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的精髓既未能在當(dāng)代中國(從‘左聯(lián)’到‘文革’)扎根,而民族文化失落感也未真正消除。有不少人都認(rèn)為現(xiàn)在又出現(xiàn)了第二次復(fù)興漢民族文化的良好契機(jī),機(jī)會與二十年代頗相似。正當(dāng)現(xiàn)代主義確實(shí)正越來越深刻地影響‘文革’后中國文學(xué)的發(fā)展之時,我想應(yīng)冷靜觀察下去:看看這種‘我們的現(xiàn)代主義’,是否又會變?yōu)橐环N新的‘我們的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’?”③許子?xùn)|的隱憂并非沒有道理,20世紀(jì)80年代末“中國式”“我們化”的現(xiàn)代主義,既是現(xiàn)代主義中國接受的塵埃落定,也是其衰落的開始,先是尋根文學(xué)思潮對民族性前所未有的強(qiáng)調(diào),后是“新寫實(shí)”文學(xué)對“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”的回歸,而曾經(jīng)被認(rèn)為是攪起語言革命、敘述革命、形式革命的先鋒文學(xué),則被認(rèn)為是“時間與地點(diǎn)的缺席”,是“‘西方主義’的癥候式表達(dá)”。④
總體而言,20世紀(jì)80年代關(guān)于現(xiàn)代主義“要不要”“好不好”“真不真”等論爭,體現(xiàn)的還是對現(xiàn)代主義的一種普適性理解,雖也在中國/西方的二元框架下,但出于“被延遲的現(xiàn)代性焦慮”,外部的中/西空間區(qū)隔轉(zhuǎn)化為內(nèi)部的“文革”“/新時期”、封建/現(xiàn)代的時間性劃界,對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/現(xiàn)代化的渴望與民族復(fù)興的民族主義激情并存,現(xiàn)代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的對抗性處于隱在狀態(tài)。但隨著80年代的終結(jié),理解現(xiàn)代性/現(xiàn)代主義的方式發(fā)生了很大變化,對過去(社會主義革命)的判斷與未來的期冀(中國向何處去)也開始分化,一種新的評判現(xiàn)代主義及其文學(xué)實(shí)踐的框架開始浮現(xiàn)。——論文作者:馬春花
相關(guān)期刊推薦:《南開學(xué)報》(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版)是南開大學(xué)主辦的人文社會科學(xué)綜合類學(xué)術(shù)期刊,創(chuàng)刊于1955年,是新中國創(chuàng)刊較早的高校文科學(xué)報之一,為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入選學(xué)報。刊發(fā)具有理論深度和學(xué)術(shù)價值的研究性文章,注意反映社會科學(xué)研究各領(lǐng)域的新成果、新信息,鼓勵創(chuàng)新,支持爭鳴,以深刻厚重的學(xué)術(shù)內(nèi)涵和嚴(yán)謹(jǐn)樸實(shí)的編輯風(fēng)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