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間:所屬分類:學術成果常識瀏覽:1次
清晨的科研交流群里,一條國自然項目結項新規的消息引發熱議 —— 導師轉發的要求中明確提到,項目研究形成的代表性論文里,國內期刊(含中英文)占比需超 20%。這一硬性指標的落地,被不少科研人解讀為“國自然大力推動國內期刊發展”的信號,而在AI領域扎堆卷國際會議、國內科研評價體系仍向“國際成果”傾斜的當下,這一政策既帶來了科研生態調整的可能,也讓研究者陷入了“合規需求”與“發展趨勢”的博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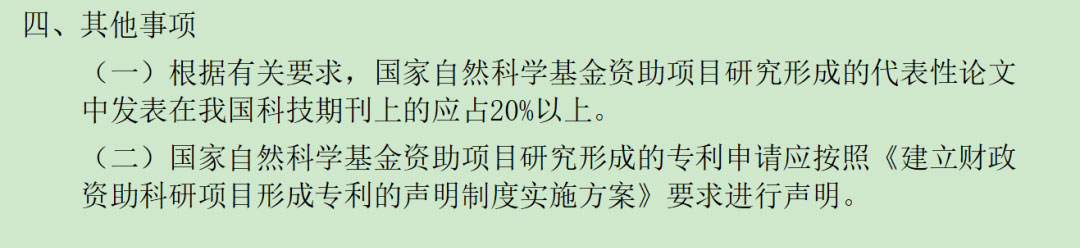
從政策初衷來看,國自然強推國內期刊并非無跡可尋。近年來,國內科研“兩頭在外”的困境始終存在:大量科研經費支撐的研究,優秀成果卻優先發表于國外期刊,后續還需高價購買數據庫獲取使用權,不僅造成資金外流,更制約了我國在關鍵學科領域的學術話語權。此次 20% 的比例要求,本質上是通過項目結項的“指揮棒”效應,引導優質成果向本土期刊回流 —— 無論是中文核心期刊,還是《細胞研究》《國家科學評論》等具備國際影響力的國內英文期刊,都有望獲得更多高水平稿件注入,進而推動國內期刊整體質量與國際認可度的提升。
但政策落地的現實阻力也顯而易見,尤其在計算機 AI 等前沿領域,“卷國際會議”早已成為行業常態。如今國際 AI 會議投稿量動輒數萬,部分會議因稿件過多導致審稿質量下滑、“水稿”爭議不斷,發展趨勢漸顯雞肋。按理說,國自然推動國內期刊的舉措,本可分流部分投稿需求,緩解國際會議的內卷壓力;可實際情況是,多數高校的畢業、評職體系仍將“國際會議/期刊成果”視為核心指標,學生若為滿足國自然結項要求多發國內期刊,可能面臨“成果不被學校認可”的困境。正如不少研究者擔憂的:導師為項目順利結項,難免會要求學生向國內期刊傾斜投稿,但這與計算機 AI 領域“以國際成果論英雄”的大趨勢相悖,最終可能讓學生陷入“結項需求”與“個人發展”的兩難。
在這樣的矛盾之下,政策帶來的市場變化已初現端倪。有研究者預測,信息科學領域的“三大學報”(《計算機學報》《軟件學報》《自動化學報》)、CCF 推薦國內期刊,以及中科院等機構重點扶持的中英文期刊,接下來的收稿量大概率會大幅提升。一方面,國自然項目團隊為達標會主動投稿;另一方面,嗅覺敏銳的科研人也會提前布局,避免后續競爭加劇導致投稿難度飆升。這種“提前卡位”的心態,背后其實是對政策與評價體系銜接不確定性的應對 —— 誰也無法預判高校何時會調整畢業標準,將國內期刊比例納入考核,只能先抓住眼前的政策導向,為成果發表留足余地。
若要讓國自然推動國內期刊的政策真正落地見效,關鍵或許在于“評價體系的協同改革”。正如不少科研人呼吁的:若學校能同步調整畢業制度,提高國內優質期刊在成果考核中的權重,讓“發國內期刊”與學生的切身利益掛鉤,才能從根本上扭轉“為結項而投稿”的被動局面,讓研究者真正愿意將高水平成果投向本土期刊。屆時,國內期刊不僅能獲得穩定的優質稿源,國際會議“內卷過剩”的問題也能得到緩解,科研生態將形成“政策引導 — 評價適配 — 成果回流 — 期刊升級”的良性循環。
國自然強推國內期刊的舉措,無疑是科研評價體系向“自主可控”轉型的重要一步,但它并非孤立的政策,需要高校、科研機構、期刊編輯部等多方協同發力。唯有打通“政策要求”與“個人發展”之間的壁壘,才能讓這一導向真正轉化為國內期刊崛起的動力,而非研究者的兩難選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