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(fā)布時間:所屬分類:法律論文瀏覽:1次
摘 要: 【摘要】話語體系的危機(jī)已經(jīng)成為我國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界不得不正視的重大問題,因?yàn)樗苯雨P(guān)系到實(shí)現(xiàn)中國自主性這一宏旨。我國的政治學(xué)研究在話語體系方面同樣存在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。學(xué)界現(xiàn)有的討論未能清晰區(qū)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:中國主位意識、學(xué)術(shù)發(fā)展階段
【摘要】話語體系的危機(jī)已經(jīng)成為我國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界不得不正視的重大問題,因?yàn)樗苯雨P(guān)系到實(shí)現(xiàn)中國自主性這一宏旨。我國的政治學(xué)研究在話語體系方面同樣存在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。學(xué)界現(xiàn)有的討論未能清晰區(qū)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:中國主位意識、學(xué)術(shù)發(fā)展階段和學(xué)術(shù)話語權(quán)。中國主位意識是話語重構(gòu)的前提,但離開學(xué)術(shù)發(fā)展階段決定的研究水平的支撐,不僅話語重構(gòu)難以完成,政治學(xué)的話語權(quán)也將難以有效拓展。這三個層面不可或缺而又互相聯(lián)系,構(gòu)成我們反思政治學(xué)話語體系的三個維度。就我國政治學(xué)現(xiàn)有的概念、理論和方法狀況而言,也可以從這三個維度展開具體剖析,進(jìn)而明確后續(xù)學(xué)術(shù)研究應(yīng)該轉(zhuǎn)型的方向。當(dāng)然,在這一努力中,也應(yīng)保持清醒的頭腦,既要尊重學(xué)術(shù)共同體和學(xué)者的自主性,也要尊重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發(fā)展的內(nèi)在規(guī)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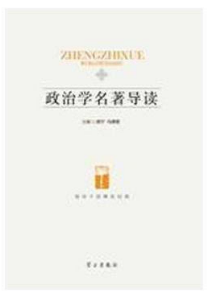
【關(guān)鍵詞】政治學(xué),話語重構(gòu),中國主位,話語權(quán),概念,理論,方法
改革開放以來,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(xué)得到了全面的恢復(fù)和發(fā)展。與此相伴隨的,一是學(xué)術(shù)主管部門和知識界共同推動的學(xué)術(shù)規(guī)范化,其中以20世紀(jì)90年代開始鄧正來等人倡導(dǎo)并實(shí)踐的學(xué)術(shù)規(guī)范化運(yùn)動為代表;二是由部分研究者倡導(dǎo)并逐漸為學(xué)術(shù)界所熟知的社會科學(xué)本土化,該取向與黨和國家提倡的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中國化形成了呼應(yīng)。從話語的角度看,無論是學(xué)術(shù)規(guī)范化,還是社會科學(xué)本土化,都意味著話語呈現(xiàn)方式和話語本身的某種重塑。
特別是本土化方面,更能體現(xiàn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的重構(gòu)訴求。就政治學(xué)而言,諸多學(xué)者都認(rèn)識到了政治學(xué)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及其面臨的問題。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學(xué)術(shù)界的這種努力來自學(xué)者自發(fā)的反思,體現(xiàn)了一定的學(xué)術(shù)自覺和文化自覺。這種反思和自覺,其實(shí)也正是我國提倡的理論研究基本原則。黨和國家的官方話語一貫強(qiáng)調(diào)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(dǎo),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、觀點(diǎn)和方法來分析并解決中國的現(xiàn)實(shí)問題;不是簡單地堅(jiān)持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教條,而是強(qiáng)調(diào)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(shí)際相結(jié)合。
毛澤東思想、鄧小平理論等黨和國家的理論結(jié)晶,均意味著政治理論的中國化,中國主位和中國的主體性都得到了強(qiáng)調(diào)。而黨和國家倡導(dǎo)的“洋為中用”的“拿來主義”,以及“古為今用”的現(xiàn)實(shí)取向,無不是我國一貫提倡的學(xué)術(shù)原則。這就是說,不管是黨和政府倡導(dǎo)與促進(jìn)的學(xué)術(shù)研究基本取向,抑或是學(xué)術(shù)界部分學(xué)者的自覺努力,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本土化一直都在進(jìn)行當(dāng)中,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話語體系也一直在重構(gòu)當(dāng)中。那么,中央近年來為何專門強(qiáng)調(diào)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話語體系問題呢?這種強(qiáng)調(diào)在什么意義上是全新的?
其中直接針對的問題和最主要的訴求又是什么?梳理習(xí)近平同志的專門講話,①可以發(fā)現(xiàn)這其中的考慮,即中央此次強(qiáng)調(diào)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話語體系問題,有著一個非常明確的訴求,即明確宣示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研究和表達(dá)中的中國主體性,并強(qiáng)調(diào)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為中國的主體性服務(wù)。這是一個統(tǒng)攝性的訴求,下面有具體的要求和指向。從政治學(xué)的角度仔細(xì)分析這種主體性訴求,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它至少意味著我國的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(dǎo)的,因而意味著批判現(xiàn)代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論范式;是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,是與中國革命、改革和建設(shè)實(shí)踐相呼應(yīng)的政治話語;是與中國崛起的現(xiàn)實(shí)和大國需要相匹配的學(xué)術(shù)話語;堅(jiān)持中國本位的立場而非以“他者”眼光為主,接續(xù)中國歷史和傳統(tǒng),將中國的政治實(shí)踐和發(fā)展道路更自主、更自信、更充分地向世界表達(dá)和呈現(xiàn)。
這種對中國主體性的宣示和強(qiáng)調(diào),顯然是一個政治導(dǎo)向,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蘊(yùn),因?yàn)樗亲非笤捳Z領(lǐng)導(dǎo)權(quán)的國家行為,意味著國家對知識和學(xué)術(shù)的某種再造。中央如此強(qiáng)調(diào)這個問題,至少說明兩點(diǎn):一是中央對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研究,尤其是其話語狀況有重構(gòu)的需求;二是中央對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的發(fā)展,尤其是其話語體系的創(chuàng)新方向是明確的。對政治學(xué)的學(xué)術(shù)話語來說,這兩點(diǎn)的針對性無疑是非常明顯的。
一、成為“問題”的政治學(xué)話語
正是因?yàn)橐鞔_地追求并貫徹中國的主體性,我國當(dāng)前的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才成為問題,或者說,才是一個急需改觀的問題。需要說明的是,為使本文的討論比較集中,本文只關(guān)注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,也就是在政治學(xué)界使用和建構(gòu)起來的話語體系。而就學(xué)術(shù)話語而言,簡單地說,主要包括概念(范疇)、理論(理念,范式)與方法(路徑,技術(shù))三大板塊。
回顧我國政治學(xué)恢復(fù)并發(fā)展的歷史,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我國政治學(xué)在概念、理論和方法這三個方面均實(shí)現(xiàn)了相當(dāng)?shù)姆e累,取得了相當(dāng)?shù)某煽儭5绻灾袊黧w性這一尺度來審視,我們又不得不承認(rèn)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存在的問題。具體到概念,政治學(xué)作為一門獨(dú)立而成熟的社會科學(xué)門類,其最經(jīng)常使用的概念具有鮮明的專業(yè)特征和學(xué)科特征。
一旦一個概念成為政治學(xué)的常用概念,它就具有了政治學(xué)特有的內(nèi)涵取向和側(cè)重。因此,政治學(xué)本身的知識譜系會產(chǎn)生一些具有政治學(xué)學(xué)科特色的概念,如權(quán)力、國家、政體、自由、民主,等等;另一方面,我們也會看到,一些概念雖然來自其他學(xué)術(shù)范疇,或是借用了其他學(xué)科的部分概念,但在政治學(xué)的學(xué)術(shù)使用上已經(jīng)實(shí)現(xiàn)了內(nèi)涵上的轉(zhuǎn)化,如結(jié)構(gòu)—功能、合法性,等等。在國內(nèi)出版物中,諸多工具書性質(zhì)的“百科全書”、“手冊”和政治學(xué)著作,對政治學(xué)基本概念都作有梳理和解釋。顯然,這些概念及相關(guān)解釋,受到歐美學(xué)術(shù)話語的重大影響,我們很難在國內(nèi)政治學(xué)討論中看到基于中國歷史和現(xiàn)實(shí)而原創(chuàng)的核心概念。
這與政治學(xué)作為現(xiàn)代學(xué)術(shù)的一個分支產(chǎn)生于西方的事實(shí)密切相關(guān),但也與我國學(xué)者在錘煉和傳播本土概念上的不足有關(guān)。在理論建構(gòu)上,所謂“理論”,就是基于事實(shí)或推演而形成的對事物間關(guān)系的一種判斷。理論有宏觀理論、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之別,也有大理論和小理論之別。形成理論、建構(gòu)理論并讓理論為讀者和同行所接受,這是學(xué)術(shù)研究在發(fā)現(xiàn)事實(shí)之外的更為重要的目標(biāo)。在每一個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史上,都會凝練出一些廣為人知、影響深遠(yuǎn)的理論或命題,這些理論或命題由于與該學(xué)科所研究的基本問題相關(guān),并深刻揭示了相關(guān)問題的內(nèi)在邏輯和本質(zhì),因此成為后來者接受或討論的焦點(diǎn)話題,對該學(xué)科的知識積累和學(xué)術(shù)成長起到非常關(guān)鍵的作用。
關(guān)于政治學(xué)學(xué)科基本的理論和定理,國內(nèi)外不少著作均已有相應(yīng)的梳理和總結(jié)。同樣,這些理論及其建構(gòu)邏輯,歐美學(xué)術(shù)話語同樣具有重大影響。我們很少見到中國傳統(tǒng)或當(dāng)代的政治理論作為政治學(xué)的主流理論或基本理論而存在。就算我們也有一些努力和貢獻(xiàn),但要么很少體現(xiàn)為大理論或宏觀理論上的貢獻(xiàn),要么只是具有地域性(主要是中國國內(nèi))影響的微觀或中觀理論。
在方法或方法論上,似乎不應(yīng)過于強(qiáng)調(diào)國別意義上的主體性,而只有方法或方法論上的成熟與否,以及運(yùn)用程度上的差異。但實(shí)際上,具體的某一或某幾種方法同樣也會限制我們的研究,甚至?xí)で覀兊慕忉專M(jìn)而影響我們對政治事實(shí)客觀全面的把握。政治學(xué)研究中存在不同層面和類別的方法。有哲學(xué)(認(rèn)識論)意義上的方法(如形而上學(xué)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),有理論范式意義上的方法(如行為主義、理性選擇與新制度主義),有分析路徑意義上的方法(如政治系統(tǒng)論與結(jié)構(gòu)—功能路徑、國家—社會路徑、國家—政黨—社會—市場的分析框架),還有研究技術(shù)和分析技術(shù)意義上的方法(如問卷調(diào)查、統(tǒng)計(jì)分析、深度訪談、田野觀察等)。
就中國主體性這個維度看,我國政治學(xué)研究方法的問題,至少有如下幾點(diǎn)值得提及:部分政治學(xué)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略有生疏或回避,而直接接軌現(xiàn)代社會科學(xué)的研究方法,由此產(chǎn)生對中國具體問題的局部解釋,而無法形成對中國政治體系與政治發(fā)展道路的縱深洞察和總體判斷;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,要么方法陳舊老套,無法跟上國內(nèi)外政治生活的新現(xiàn)實(shí),要么一味追求分析技術(shù)上的前沿和新潮,而忽視中國語境下政治事實(shí)的本來面目;在研究路徑和分析方法上,要么將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個案,運(yùn)用通用方法來驗(yàn)證已有的政治學(xué)理論,要么將中國作為一個另類政體,而只傾向于問題化地研究中國政治,進(jìn)而忽視了研究方法的適切性。
總之,從中國主體性的高度審視,我國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中的概念、理論和方法都存在結(jié)構(gòu)性的缺陷。在我國政治學(xué)研究中,自主生產(chǎn)概念、建構(gòu)理論、創(chuàng)新方法的能力總體上偏弱,而簡單采用來自歐美的概念、理論和方法的現(xiàn)象依然嚴(yán)重。
問題是,現(xiàn)成的政治學(xué)概念、理論和方法本來有其獨(dú)特的經(jīng)驗(yàn)基礎(chǔ),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釋中國政治的內(nèi)在邏輯或運(yùn)用于對中國政治的分析中,更不能有效地支持中國政治的未來建構(gòu)。特別是在采用那些明顯具有價值偏好或意識形態(tài)色彩的概念或理論時,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簡單采用了“他者”的立場,對中國政治的特殊性未能充分審視,對中國政治的正當(dāng)性未能充分認(rèn)知。
由此導(dǎo)致了政治學(xué)的學(xué)術(shù)表達(dá)與政治現(xiàn)實(shí)之間的巨大裂痕:要么無法呈現(xiàn)政治事實(shí),要么片面呈現(xiàn)政治事實(shí),要么虛構(gòu)了并不存在的政治事實(shí)。而在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與中國政治實(shí)踐和政治經(jīng)驗(yàn)的關(guān)系上,解釋性話語明顯不及批判性的話語,政治學(xué)話語的正當(dāng)化功能尤顯不足。雖然不能否認(rèn)學(xué)者的研究應(yīng)該獨(dú)立,并應(yīng)具有一定的批判性,但批判應(yīng)該在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實(shí)之后進(jìn)行,而不是純粹從理念或分析框架出發(fā),簡單地批判現(xiàn)實(shí)并建構(gòu)中國政治的未來。
不可否認(rèn),面對黨和國家的急切需要,面對國內(nèi)外政治諸領(lǐng)域的現(xiàn)實(shí)變化,我們的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多少顯得供給乏力,或是供給錯位。現(xiàn)有的政治學(xué)話語,對中國政治發(fā)展道路的解釋力不足,對黨和國家政治決策的貢獻(xiàn)度有限,對其他社會科學(xué)學(xué)科的影響力有限,對社會輿論和公眾的引導(dǎo)力更是微弱。特別是在某種意義上,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最集中地體現(xiàn)了我國在“挨罵”問題上的被動性。也就是說,本來我們在政治上做對了很多事,但在話語上依然沒有有效地研究和呈現(xiàn)。因此,對黨和政府來說,要解決“挨罵”的問題,就有必要倡導(dǎo)重構(gòu)政治學(xué)話語;就政治學(xué)界來說,要使研究實(shí)現(xiàn)真正的轉(zhuǎn)型與升級,同樣需要重構(gòu)學(xué)術(shù)話語。
當(dāng)前,在我國的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界,話語體系的創(chuàng)新和重構(gòu)正在轟轟烈烈地推進(jìn)著。如本文前面所檢視的,我國的政治學(xué)話語在中國主位意識、研究水平和話語權(quán)三個層面,均存在亟待反思和正視的問題。因而,需要在政治學(xué)話語體系中的概念、理論和方法上作相應(yīng)的改進(jìn)。只有這樣,才能創(chuàng)新政治學(xué)話語體系,貢獻(xiàn)于國家的政治話語權(quán)。但也要看到,目前追求話語權(quán)、促進(jìn)話語重構(gòu)的過程,也容易使學(xué)術(shù)研究具有偏向性和選擇性。這樣也可能會形成對西方政治世界的新偏見,和對本國政治的封閉的自我認(rèn)知。這無疑是值得警惕的。
同時,在研究的積累性、傳承性和學(xué)理性不足的情況下,短期內(nèi)拔苗助長地推動話語體系更新,可能會立不住,沉淀不下來。這里尤其需要尊重學(xué)術(shù)共同體的自主性和學(xué)者的自主性,并對政治學(xué)話語體系的創(chuàng)新保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。學(xué)術(shù)探索有自身的周期和規(guī)律,外力的刺激或干預(yù)并不能脫離這種周期和規(guī)律的制約。社會科學(xué)的學(xué)術(shù)探索既要全面深入地梳理、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,又要深入到研究對象本身,作大量的調(diào)查研究或文本解讀,更需要獨(dú)立的思考和廣闊視野下的比較。
只有這樣,才有可能發(fā)現(xiàn)新的事實(shí),提煉新的概念,構(gòu)建新的理論。而無論是學(xué)術(shù)探索的哪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,都需要長期的積累。話語重構(gòu)若要真正經(jīng)得起時間和學(xué)術(shù)共同體的檢驗(yàn),就要有相當(dāng)?shù)哪托暮妥鹬亍L貏e是對政治學(xué)的話語重構(gòu)和研究轉(zhuǎn)型而言,小到概念和提法上的變化,中到機(jī)制分析,大到政治理論的建構(gòu),都不能拔苗助長,通過急功近利的各種方式去刺激。
實(shí)際上,政治學(xué)學(xué)術(shù)共同體若能夠基于學(xué)術(shù)研究自身的規(guī)律,不斷地探索和積累,基于話語重構(gòu)的研究轉(zhuǎn)型就會水到渠成。否則,那種通過人為“打造”和“制造”的話語重構(gòu),特別是沒有相應(yīng)學(xué)術(shù)積累的偽研究,將不僅損害政治學(xué)者和政治學(xué)共同體的良性成長,從長遠(yuǎn)來看更會損害國家的文化軟實(shí)力。